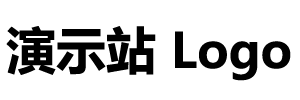轉基因魚安全!專家:中國早該推轉基因食物
11月19日,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準轉基因三文魚(學名為大西洋鮭魚)上市,成為全球第一個進入市場的轉基因動物食品。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再次引發了人們廣泛熱烈的爭論。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轉基因魚類科研領域,中國科學家一直處于最前沿。
1984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領銜的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下稱中科院水生所)團隊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批轉基因魚,隨后建立了轉基因魚理論模型,構建了由鯉魚和草魚基因組件組成的、擁有全部自主知識產權的重組生長激素基因并培育出快速生長的轉“全魚”基因黃河鯉魚和不育三倍體“863吉鯉”。
但其后的三十年中,轉基因黃河鯉魚卻在公共視野中默默無聞,甚至朱作言本人如今也對其市場化感到沒有信心。
11月24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朱作言透露,在上市這條路上,轉基因黃河鯉魚甚至一度有希望登陸美國。2000年的時候,培育轉基因三文魚的美國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第一任總裁埃利奧特·恩提斯曾到武漢,拜訪朱作言當時所在的中科院水生所,尋求合作可能性。
從1985年至今,轉基因黃河鯉魚經歷漫長的試驗和審批過程,至今仍處于環境釋放實驗階段,通過了這一關之后,還需要進行生產性養殖實驗才能拿到安全證書,其后還需要申請品種認定才能正式上市。“轉基因黃河鯉魚,還遠著呢。”朱作言感嘆說。
中國轉基因魚曾是美國的“老師”
埃里克•哈勒曼是弗吉尼亞理工大學魚類保育系主任,也是最早的一批轉基因魚類研究者。2015年9月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他認為朱作言的研究后來做得更好。
“那時候教我做微注射的人還是朱作言。他曾經用那種像嬰兒毛發一樣細的工具來做魚卵注射。我當時說,這太復雜了,我們想辦法改進一下針和流程吧。在和中國同行的合作中,我們不但一起做出了更好的注射系統,也開始注意到一些后來證明非常重要的課題。”埃里克•哈勒曼說。
所謂“微注射”即用顯微操縱器將外源DNA等直接引入靶細胞,朱作言說,轉基因黃河鯉魚即將草魚生長激素的基因拿出來,經過改造轉移到黃河鯉魚身體中,也就是說黃河鯉魚是帶有草魚生長激素基因的黃河鯉魚。
“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把草魚的一個基因放到鯉魚里面去了。”朱作言解釋說。生長激素基因通常被簡稱為GH基因,目前仍是轉基因魚類研究的主要關注方向,而美國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的轉基因三文魚也是轉入了GH基因。
據報道,轉入GH基因的三文魚能夠比野生三文魚更高水平地表達一種生長激素,這種轉基因魚長足尺寸只需18個月而非3年。朱作言介紹,轉基因黃河鯉魚的效用同樣也是將生長期需要兩三年才能上市的黃河鯉魚縮短到一年。
“養魚時間越長,養殖戶們越提心吊膽,隨時可能出現風險,比如說疾病,災害,水體污染等。一畝魚池養一年的時間可以產出兩年的量,相對就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和時間的成本。”朱作言說。
“營養和安全性都沒變”
但速生的轉基因魚類的營養價值和食用安全性,是否會有所改變?
“做安全評價的時候,營養學的指標也是一個重大的指標。如果說它跟過去改造之前不一樣了,它也不會獲批。”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云波對記者表示,GH轉基因魚類生長發育雖然速度加快,但營養的積累也是隨著生長一塊發生的,因此其營養價值不會降低。
另外,轉基因黃河鯉魚選擇轉入草魚的GH基因,主要原因就是兩種魚其實本身是可以雜交的。“轉基因鯉魚就是把草魚2萬多條的基因中的一條基因拿出來,放到里面和鯉魚去雜交,從雜交程度上來說,它只相當于鯉魚和草魚雜交的兩萬分之一不到。
如果我把草魚和鯉魚的雜交品種拿到市場上去,不會有人懷疑這個魚是能吃還是不能吃,不會有人想吃了有沒有危險。”對于轉基因鯉魚的食用安全性,朱作言認為與草魚鯉魚雜交品種相同。
“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態安全與食品安全方面的顧慮,同時也為了提高基因表達效率與生理功能的發揮,經濟魚類的轉GH基因研究中所采用的轉基因元件,包括GH基因、調控GH基因轉錄的啟動子及轉錄終止子均來源于魚類,即‘全魚’基因或‘自源’基因。”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研究員葉星對澎湃新聞解釋說。
遺憾研究沒有轉化成生產力
除了食用的安全性,轉基因生物對于生態環境是否安全也是能否投入生產的重要考量。“轉基因的物種,不管是動物還是植物,一旦從實驗室中釋放出去,不管你在種植或養殖的過程中多么注意,它依然是會有生態污染的風險的。
因為轉基因三文魚是第一個被批準商業化的轉基因動物,我們也無從考證這方面的案例,但是植物方面污染的案例是非常多,比如之前北美農場的轉基因小麥,后來被發現對農場造成了污染,所以轉基因三文魚依然在生長過程中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張菁對澎湃新聞分析說。
葉星2011年5月發表在《遺傳》雜志的論文中認為,“生態安全方面的擔心是轉基因魚具有較快的生長速度,較強的抗病力、抗逆性,可能比野生型魚或其他物種更具適應性和競爭力, 一旦釋放或逃逸到自然環境中,可能破壞原有的種群生態平衡,甚至導致某些野生品種的滅亡、威脅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另一方面, 轉基因魚可能與野生近緣種雜交導致‘基因逃逸’,造成野生物種的‘基因污染’。
因此,在商用化之前需要對轉基因魚進行生態風險評估,通過評估比較轉基因魚與野生型魚對環境的適合度,預測轉基因魚釋放或逃逸到自然水體后可能產生的潛在生態風險。”
朱作言表示,據他了解,除了通過隔離飼養、培育不育的轉基因三文魚之外,美國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還特意選擇了巴拿馬的一個高原進行養殖。“上面溫度很低,三文魚需要水溫比較冷,但如果他隨著河流流下來,因為下面河流的溫度比較高,所以這些三文魚即使逃到河里也存活不了。”朱作言說。
但對于對環境要求不高的鯉魚來說,這樣的做法似乎并不可行。“不同對象最后所采取的措施的完備程度,我們覺得我們的實驗比較好。”朱作言介紹說,在轉基因魚類絕育和生態系統試驗方面,轉基因黃河鯉魚比轉基因三文魚做的更為完備。
朱作言解釋,在絕育方面,轉基因黃河鯉魚能夠成為百分百的“三倍體”(因含有三組染色體而不育),就算逃逸也不會造成生態的污染,而轉基因三文魚因為采用不同的技術,尚不能做到百分百的“三倍體”。而在生態系統試驗方面,中科院水生所的研究人員在一個100畝的人工湖里模擬了長江中下游的生態系統,然后將轉基因黃河鯉魚放入,經過5年試驗后發現,轉基因鯉魚逃避風險的能力更差,動作也比正常鯉魚笨拙,超出了研究者的預期。
“原來是擔心它越來越多侵占別人的領地,結果最后它越來越孤單,五年后變得很少了。所以,即便逃出去以后,它要繁殖也很難繁殖得起來。”朱作言說,類似這樣的研究他在轉基因三文魚那里沒有看到,“還有一些更細、更具體、更深入、更系統的研究他們也沒有,但我們的研究沒有轉化成為生產力,是非常遺憾的。”
美國公司曾提合作促中國轉基因魚上市
朱作言1984年完成的第一個轉基因魚模型來自于泥鰍和金魚。隨后,世界各國許多實驗室在短短幾年中,使用多種人工構建的外源基因,在鯉、鯽、虹鱒、鯰、斑馬魚、羅非魚、大西洋鮭、大馬哈魚等近20種魚類上進行了轉基因研究。
朱作言向記者表示,中科院水生所團隊從1994年開始轉做轉基因黃河鯉魚的實驗,并且在2000年完成中試(中等實驗)。在2000年,美國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的總裁埃利奧特·恩提斯來訪,希望能共同合作。“他希望我們共同做,他也知道我們做得好,因為我們比他們做得早,他也希望考察一下這個鯉魚將來在美國有沒有市場。”朱作言說,遺憾的是,美國人認為鯉魚并不適合美國市場。
“現在轉基因三文魚的研究也是加拿大科學家做的,生產也在加拿大,只是由美國公司接手過去了,這在中國是很難想象的。”朱作言解釋說。
朱作言回憶,轉基因黃河鯉魚項目在最初的時候,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政府都對此有濃厚興趣。項目得到了863計劃的支持,得到中科院的支持,也得到湖北省政府的支持,湖北省科委甚至主動要求先在湖北進行試驗。
2002年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實施之后,轉基因動植物產品的生產和上市管理趨于嚴格,轉基因黃河鯉魚在此之前并沒有抓住時機獲得上市的機會。
“中國要成為第一個批準轉基因動物食品的國家,當時并沒有這樣的魄力和勇氣,公眾的理解也比較缺乏。我們的研究走在前面,但是對市場化沒有信心。”朱作言說,沒有企業的介入,科學家只算是踏出了第一步,“我們沒有時間一天到晚去政府部門跑,也沒有這樣做,所以也不能怪政府不批準。如果你不反復去跑部委的話,那是沒辦法。”
按照農業部2002年施行的《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轉基因動物要進行品種審定,要首先取得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要取得安全證書,必須經過實驗室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安全證書申報等5個階段。
轉基因黃河鯉魚如今仍在準備做環境釋放實驗階段
“由我們自己研制的主要的轉基因食品現在還沒有真正用于生產的。FDA宣布美國市場轉基因三文魚準入后,反應也很平淡,不像(國內)鋪天蓋地的反對聲就來了。說明(美國)從民眾的承受能力、科學素養,對新技術接受的心態比我們社會要成熟,畢竟美國是個新技術層出不窮的國家。”朱作言說。
快速生長的轉基因黃河鯉魚(上)及其對照黃河鯉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