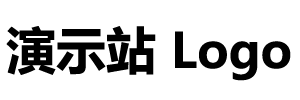霸王別姬電影劇情詳解(陳凱歌導演電影《霸王別姬》解讀)
電影《霸王別姬》解讀
導演:陳凱歌
主演:張國榮/張豐毅
地區:中國
上映時間:1993年
《霸王別姬》
一、主題分析
《霸王別姬》這部電影的內容相當復雜,不僅外籍人士因文化、背景差異在看法上有相當不同,國內觀眾看了也幾乎觀點各異:有人看了大聲喊好,但好在何處又說不清楚;有人說這電影根本不好嗎,只是對意大利導演貝爾托魯齊的《末代皇帝》的模仿,水平遠遠趕不上張藝謀導演的《活著》,也有人說這部影片遠超那部影片之上;有人覺得這部電影很容易就能懂,也有人說這部影片解讀起來有相當的難度;有人則認為這部電影是在顯示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更有人認為這部電影主要在控訴“文革”;也有人說這部電影主要描寫的是演虞姬的小豆子(程蝶衣)如何在從小到大的一生中尋找認同的過程。有人認為這片有“美化暴力”的嫌疑(如把學戲的孩子們打的這么慘。以及“文革”的火紅場面等)多數人們認為這片的主要角色是飾演虞姬的程蝶衣,但也有人認為本片主角是飾霸王的段小樓,也有人認為本片主角是段小樓、程蝶衣、菊仙三位,缺一不可,平分秋色。來自美國的消息說,一位中年的美國朋友在看了此片后對京劇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同情,像他這樣的西方觀眾并不在少數。美國的一所大學的大學生報對這片的影評是:其中每個角色的演出皆是一流的,導演能處理片中這么多困難的角色和情節難得的,相比之下,貝爾托魯齊的《末代皇帝》雖也不錯,但顯得就像個卡通片。這片的英文名稱是《Farewell My Concubine》。該報說這部戲的主角(飾虞姬的程蝶衣)真也就不分臺上臺下,“戲夢人生”地真想當起Concubine(妾侍)來。該報同時也說程蝶衣“肢體語言”的演出很上乘。
程蝶衣
應該說,《霸王別姬》一片感情強烈、情節曲折,充滿生生死死的觀劇沖突,并邀請幾位大明星主演,具備充分的商業元素,同時又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在這一點上,與陳凱歌的前作既一以貫之又有所超越。香港影評界對本片用“雅俗共賞”叫好又叫座、以“通俗中見斑斕,曲高而和者眾”來形容是相當中肯的。
陳凱歌選擇中國文化積淀最深厚的京劇藝術及其藝人的生活來表現他對傳統文化、人的生存狀態及人性的思考與領悟,這是很聰明而獨到的。國際影評聯盟評委認為:“《霸王別姬》一片深刻挖掘中國文化歷史及人性,影像華麗、劇情細膩”。這是外國專家的看法,對于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人來說,此片的內蘊更為豐富深廣,銀幕影像的張力更具歷史深度。
陳凱歌導演
那么影片究竟在表現什么,這要從情節編碼中方可讀出。
從表層看,影片《霸王別姬》寫的是兩個京劇男演員與一個妓女的情感故事,“這種情感綿延50年,其中經歷了中國社會的滄桑巨變,也經歷了他們之間情感的巨變與命運的巨變——由張國榮扮演的青衣演員程蝶衣,他是一個在現實生活中做夢的人,在他個人世界里,理想與現實、舞臺與人生、男與女、真與幻、生與死的界限統統被融合了,以致當他最后拔劍自刎時,我們仍然覺得在看一出美麗的戲劇,這個人物形像告訴我們什么叫迷戀。”陳凱歌說。
的確,從這個角度看,《霸王別姬》一片基本上講述的是一個有關人生與情感的故事,講述一個沒法將人生與藝術區分開來的浪漫理想主義者的悲劇。這個人物如同追求愛情一般的獻身理想和藝術,還有感情,最后為藝術、感情而凄美獻身。可以說,他寧愿死在戲中,也不想活在真實里,寧可糊涂,也不要清醒。他到死都“執迷不悟”,為著成全自己,掙扎著與命運做著蚍蜉撼樹、螳臂擋車式的無望之爭,最終成為信仰的祭品。然而,這種執著的精神和為藝術、感情獻身的勇氣卻使他的生活體現出一種精彩與美麗。
《貴妃醉酒》
然而從深層看,我們發現問題并不是那么簡單:透過陳蝶衣的悲劇,我們不難發現,《霸王別姬》片在嚴密的敘事背后,是導演以懷疑、批判的理性視角對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及人的生存狀態、人的命運表示了深切的關注和潛在憂慮。
任何一個主題想要完美地被體現,需要由情節編碼來體現,那么《霸王別姬》一片都作了哪些情節編碼的鋪陳呢?
故事一開始,是清末民初的北洋時代,(透過全片,我們有理由相信,假如不是人物的年齡限制了他們存的時代,沒準陳凱歌他們會把段小樓和程蝶衣放在清朝、明朝,甚至跨越整個中國的封建時代里去,因為只有這樣才更容易、更清晰地表現他要表現的主旨,正因為此,在這一段中,北洋時期的人物并未成主角,恰是清室子弟那坤和張公公唱了主戲)當剛京劇風行,用片中關師傅的話說,叫“是人的就得聽戲,不聽戲的就不是人”,關師傅還說“哪朝哪代京劇也沒這么火過,你們算是趕上好時候啦!”所有的學藝者便異口同聲地回答:“沒錯!”
小豆子
一方面是殘酷地學藝,另一方面成角以后也確實會達到萬人敬仰的效果。小賴子、小豆子吃不了學藝的苦,逃出戲班后,又被京劇藝術的魅力感染,更被京劇演出時的火爆現場氣氛震撼,冒著被打的危險,再次回到戲班,也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關師傅話的正確。
話說回來,當時的京劇再紅火,程蝶衣和段小樓合演的《霸王別姬》也只是作了太監張公公的堂戲而已,小豆子還成了狎玩的對象,用那坤的話說,叫“這虞姬再怎么演,她也難逃一死不是?”
程蝶衣和段小樓
同樣,在日軍侵華期間及抗戰結束國民黨統治時期,京劇依然是半肢半癱的藝術,依舊作為滿足權力(日軍官青木三郎、國民黨要員等)觀看快感的玩意。就是捧角權貴袁四爺,精通戲理的表象所隱藏的依然是狎玩心理。藝術(京劇)在權力支撐的高奏封建主義旋律的歷史舞臺上不過是充當了粉飾和娛樂用的道具。
但即使如此,藝術和藝人在這個時期,盡管艱難,畢竟頑強生存。難忘全劇的一個高潮戲、程蝶衣因為給日本人唱戲被法庭審判,袁四爺傾力相救,終因程蝶衣心如止水而功虧一簣,眾人皆以為蝶衣此次必死無疑,卻不想峰回路轉,又見生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藝人的地位提高了,對藝術的感染力量也更加重視了,但是對文藝的宣傳教化功能的過于強調,以及賦予藝術不該承受的重中之重,結果讓古老的藝術不是煥發了青春,而是一度走進了瀕臨凋零。
由此可見,《霸王別姬》中的真正主角既不是歷史也不是程蝶衣或段小樓,而是京劇。而京劇,由于“融傳統的文學、音樂、舞蹈、繪畫、曲藝,雜技于一爐,集中國獨樹一幟的寫意美學體系之精粹于一身”,在影片里“因之就具有中國傳統藝術乃到中國傳統文化象征的意蘊。”
二、攝影分析
京劇《貴妃醉酒》
陳凱歌在本片充滿激情的敘述這個延續半個世紀的故事,但他卻不滿足于僅僅動人地講故事。片中一些鏡頭極具張力,具有相當大的歷史涵蓋面,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像影片一開始,鏡頭緊跟“霸王”和“虞姬”緩步走進體育場,長長的過道,相對固定的拍攝距離,使這樣一個運動鏡頭產生了“動中取靜”的沉重壓抑感,一下了將人帶進真幻難辨的氛圍里,恍若隔世一般。另一場小豆子被母親砍斷手指,疼痛難忍,在戲園子里奔跑大叫,其余角色在不同精深位置也相應的急速轉動,劇烈狂暴的畫面處理再配以撕心裂肺的尖叫、可謂先聲奪人——學戲之艱難嚴苛,從導演安排的這個下馬威便足見一斑了。再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小四取代程蝶衣扮演虞姬,程蝶衣忍痛接過師兄弟們傳遞過來的霸王頭飾為段小樓戴上一場。動作連貫,一氣呵成,長鏡頭完整地展現出極具真實感的空間布景,加強了影片的節奏與流動感。
用光與用色上,導演和攝影也是非常講究。如花滿樓相親一場,鋪大蓋地的大紅色調幾乎能把銀幕點燃,而程蝶衣和袁四爺扮裝調戲的場面則用清冷陰郁的調子,加上淡淡的放煙效果,醉后漫舞,雌雄難分,真假莫測,一派迷離景象。
三、聲音分析
(一〕京劇演出片段
程蝶衣
影片中選用的幾個京劇的片斷是經過嚴格精選的,陳凱歌說是要“盡量借這些片斷說明程、菊及段三人關系的變化升”。但事實上,不單如此,這些京劇片斷對于塑造程蝶衣的形象是極具魅力和讀解意義的符號視聽元素。
小豆子完成了由男兒郎到女嬌娥的轉變,來到張公公府上第一次演出“虞姬”,唱出了本片的主題唱詞:“自從我隨大王東征西戰,受風霜與勞碌年復年年……恨只恨無道秦把生靈涂炭……”此時的唱詞既涵盡了小豆了練戲的辛酸,也第一次強制性地將本片主題唱詞《霸王別姬》的內容灌輸給了觀眾。
《霸王別姬》的第二次演出是兩人成角兒以后,這場戲將兩人爐火純青演技表現得酣暢淋漓,臺下觀眾歡呼雀躍,一片沸騰。同時,本場也交代了袁四爺的出場,更將程蝶衣與段小樓的微妙情感矛盾突顯在戲后卸裝的鏡像之中。
菊仙準備嫁給段小樓,來到戲院聽段小樓唱戲。臺上,段小樓和程蝶衣唱的臺詞正是:“今日是你我分別之日了。”預言了段小樓、程蝶衣即將分開的未來走勢。
菊仙
段小樓與菊仙成親后,感到絕望的程蝶衣在袁四爺處唱的詞是:“漢軍已掠地,四面楚歌,君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時,“漢軍”成了菊仙(世俗生活)的象征。這個“漢軍”讓程蝶衣肝腸寸斷,有了自殺的念頭。如果小是袁四爺的適時提醒“這可是真家伙”,沒準此時程蝶衣就可能命喪黃泉。
日本兵占領北平,程蝶衣為他們唱的是《貴妃醉酒》一段,其中的重點唱詞是:“……啐,哪個與你通宵?”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戲是菊仙和段小樓的結婚大典。這句唱詞恰到好處地象征了程蝶衣難與段小樓、菊仙共處的心境——“人生在世入春夢,且自開懷飲幾盅。”
在這場戲里,程蝶衣在傳單飄落時以及停電時照唱、照演、照舞,顯示出程蝶衣只知藝術,不論國別與政治的簡單思維與心態。而袁四爺率先從座位上立起鼓掌的情節也明確了他作為另一個“戲癡、戲迷、戲瘋子”的身份。他是在為藝術的獨立性而鼓掌,是在為程蝶衣無論國別、政治、民族而鼓呼。這場戲跟下一場亦即日軍進駐北平后段小樓怒砸漢奸被捕,為了救段小樓,程蝶衣來到日軍司令部為其演唱《牡丹亭一游園》一折是一脈相承的:“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于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賞心樂事誰家院?”這一段尤其是最后一句更加突出了程蝶衣為藝術而藝術的特點。
《牡丹亭》
為國民黨軍隊唱的戲文同樣如此:“不到園里怎知春色如許,”聯想到前面的臺詞:“外面時代不好,但我們太太平平地唱戲就行了”,這一切顯示出程蝶衣只想讓藝術獨立于世俗政治之外不想負載其他的念頭。
北平解放,兩人為解放軍演唱,唱的詞是“大王慷慨悲歌,令人淚下,待妾妃歌舞一回,聊以解優如何……”此時的味道多么像一個怨婦,他們還是想把文藝當成個娛樂消遣的工具,然而,卻怎么也唱不下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號召戲劇改革,程蝶衣因此與小四發生沖突,結果會議決定換下程蝶衣,讓小四份演虞姬。而這一切程蝶衣卻蒙在鼓里。還在認真在對鏡描妝,做著上臺的準備,直到在鏡里看到另一個虞姬款款走來,準備上場,他愣住了,迎上剛從臺上走下來的“霸王”段小樓,顫抖的聲音問他是否知曉,段小樓囁嚅不語,小四冷言相譏,段小樓口里說著罷演,卻并不真的行動……當適時也,“虞姬”肝腸寸斷,他顫抖著手為“霸王”戴上戲帽,那一刻,從舞臺傳來小四的畫外演唱:“恨只恨無道秦把生靈涂炭,只害的眾百姓痛苦顛連”,正是對這一場景的血淚控訴,當“虞姬”黯然神傷準備離開戲院時,畫外恰逢其時地傳來了“霸王”的演唱:“此一番連累你多受驚慌……”此情、此景、此聲、此話,渾然天成、撼人心魄,將一場戲中戲挑上了高潮。
當菊仙懸梁自盡,畫外傳來那個年代京劇《紅燈記》里的李鐵梅的演唱:“聽奶奶講革命,英勇悲壯,卻原來是……(風里生雨里長)”,這一句詞道盡了“文革”反文血雨腥風的真諦,令人悲從中來,俘想聯翩……
“四人幫”粉碎了,程蝶衣和段小樓再上舞臺,雖然“文革”是過去了,日了應該和以前有所不同了,但經歷了政治年代血與火洗禮的程蝶衣知道,他的藝術生涯己經走到了盡頭,愛情也到了劃句點的時候,所以他毅然決然,拔劍自刎, “從一而終”,“自個兒成全了自個兒。”
至于昆曲《思凡》,所謂“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師傅剔去了頭發。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為何腰系黃絳,身穿直裰?看人家夫妻們灑落,一對對著錦穿羅,不由人心急似火,奴將袈裟扯破……”更是在片中多次出現,它有力地突出了程蝶衣這個人戲不分的瘋子、這個愛上了不該愛的人的癡人、這個恍恍惚惚把自己當成了“虞姬”的人、在由“男兒郎”向“女嬌娥”的轉變中是一個多么痛苦的過程,自從被送到了戲班的那個時刻起,共被戕害的命運便已經被決定了。
《思凡》
《思凡》第一次在本片出現,是教戲的師傅考問的時候,小豆干將戲文說錯。其結果是挨了一次重重的打,滿手鮮血。他絕望之極,將手伸向滾燙的熱水以求自殘了斷這痛苦不堪的學戲生涯,此時,畫外響起“磨剪子鏘菜刀”的叫喊,這個叫喊同樣出現在小豆子被母親殘忍剁掉多余的第六個手指那一場,使這一場與前一場無疑具有相同的粗戕害意義。
第二次是那坤為張公公選戲時,小豆子再次將戲文背錯。“我叫你錯、錯、錯!”段小樓一臉痛苦的地用水煙袋捅進了程蝶衣的嘴里,隨著京劇的鼓點,血流了出來!小豆子突然似乎悟了什么,他含血帶笑,款款走向鏡頭,儀態萬方、行云流水般道出了“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居然一字不差的背出了戲詞,于是大家都松了口氣,小豆子開竅了,可以不用挨打了!然而另一種異樣的辛酸卻從心里緩緩溢出。
小石頭作為暴力的實施者、抄起師傅的煙袋鍋在小豆子的嘴里一陣狂攪,實現了小豆子被改寫的最后一筆,從那一刻起,注定程蝶衣是為這“國粹”分不清人在戲中抑或是戲在人中。從那一刻起,他開始自覺地“自個兒成全自個兒”,從那一刻起,人無論如何努力也抗不過天命。
少年蝶衣
再后來,“文革”結束后空蕩蕩的舞臺上,程蝶衣、段小樓出演了將影片悲劇推向高潮的一幕:先是段小樓發現自己在長期不練功后,演技已不靈光。接下來仿佛希望程蝶衣回憶以往舊情一般念出了“小尼姑年方二八”的詞句,沒想到程蝶衣在與他對詞時又一次犯錯:“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當段小樓指責他“錯了,又錯了”的時候,他愁腸百轉、思緒萬千。接下來,當聽到段小樓問“漢軍”在哪里時,他平靜如止水,猛地抽出那柄寶劍,在“虞姬”刎頸的時刻自殺身亡。如果這是顛倒、聲討歷史的時刻,那么這又是完滿歷史鏡像的時刻;如果這是歷史延伸向現實的一瞬,那么現實卻是一片空白。
是誰讓程蝶衣錯,是誰讓京劇錯?“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在這兒具有藝術本不該附于任何強權的讀解意味。
(二)戲外音樂音響
本片的音樂是很到位的,恰到好處地介入了劇情,渲染了氣氛和節責。如小豆子被送到張公公府一場,當張公公向小豆子撲過來時,音樂聲陡然加強,令人揪緊了心,為小豆子不幸的命運而牽腸掛肚。
張公公府上演出
程蝶衣成角兒后,無時無刻不思念兒時的玩伴小癲子。當他和段小樓在萬人擁護中走進那個當年他們看別人演戲的戲園子,以及從戲園了走出,影片兩次安排他的耳際響起了糖葫蘆的叫賣聲,這令人不禁回想起那非人的歲月,如果小癲子能受得了那頓打,他是否也會像程蝶衣一樣成為眾星捧月的角兒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程蝶衣、段小樓、小四等開會討論京劇改革的問題,導演將此場戲選在一個嘈雜的戲院環境,當與段小樓站起來準備附和程蝶衣的言論時,菊仙扔給他一把傘,這時,畫外嘈雜的聲音猛然加大了,砸釘子的聲音及電話鈴聲一聲緊似一聲、一陣緊似一陣,這聲聲如重錘砸在段小樓的身上、心上。在這里,現實環境作為心理因素巧妙地介入劇作因素中,一石兩鳥,相得益彰。
四、道具分析
(一)劍
劍
劍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現是段小樓與程蝶衣為張公公演出之后,在張公公的府邸發現了這把劍,段小樓說:“霸王要是有了這把劍,早就把劉邦給宰了。”如果“霸王”能斬劉邦,那意味著“虞姬”可以永生,“可以成正宮娘娘。”于是小豆子馬上表態說:“師哥,我準送你這把劍。”一句臺詞將小豆子希望永遠依傍小石頭,希望永遠得到小石頭保護的心態表現得淋漓盡致。
劍第二次出現是段小樓與菊仙成親的時候。程蝶衣投身袁四爺,從袁四爺出將劍要到手,送給段小樓。此時的陳蝶衣多么希望段小樓能再次擔當起“霸王”的重任,然而,酒醉的段小樓對此渾然不知,在道了一聲“好劍”之后,懵懵懂懂的說:“又不上臺,要劍干什么?”程蝶衣聽了,無限失望、無限絕望,臨走告訴段小樓說:“從今往后,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兩人自此分道揚鑣。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把劍外化了兩人的隔膜與沖突。
劍第三次出現是日本人占了北平后。段小樓因為棄唱玩蛐蛐而變得心情異常煩躁.這時,菊仙告訴他,關師傅要見他,他一聽,表面上說無臉見師傅,內心里卻是無比興奮,于是拿出劍來舞了一通,他知道師傅找他是讓他繼續回到戲中,
他感到重新回到舞臺的希望,他要重新當“霸王”。
劍第四次出現是程蝶衣被國民黨軍隊以漢奸罪抓住問罪的時候。為了救程蝶衣,段小樓和那坤去求袁四爺、反遭了袁四爺的一同奚落。在袁四爺的一句“應該他去救虞姬啊”的話中,段小樓既尷尬又困窘。這時,菊仙來到,將劍送回袁四爺處,并說:“這劍找著主兒,我也就放心了。”此時,真如袁四爺所問,到底段小樓是“霸王”,還是四爺是“霸王”?又究竟是誰才能擔當起保護虞姬的重任呢?真是“人哪,也總有指望錯的時候,”段小樓就這樣被菊仙給卸了任,而這根本不是程蝶衣之所愿。而對此情此景,哀莫大于心死,所以程蝶衣才在法庭上喊:“你殺了我吧!”
程蝶衣段小樓
劍第五次出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前夕,小四秉程蝶衣之意將劍又給了段小樓,而那坤在一旁添油加醋的話無疑加重了此番動作的味道:“趕緊的.不然劉邦就殺進城來了。”段小樓再次擔當起保護虞姬的“霸王”重任,而此時“劉邦”一詞無疑有助于理解程蝶衣最后自殺時“漢軍”的所指意義。
劍第六次出現是小四拷問段小樓的時候,這時的劍不但救不了“虞姬”,反而成了懸在自己頭上的一個達摩克里斯之劍,段小樓連自身也難保了。
之后是批斗會,在重壓之下,“霸王”徹底地向“劉邦”表示了忠心與臣服,他把本該殺“劉邦”的劍扔進了火中。菊仙驚詫于“霸王”的徹底轉變,也明白連“虞姬”都不會保護的“霸王”當然不會保護自己,于是沖上前將劍取出,走完了她的風凰涅槃前的最后一步。
劍最后一次出現是段小樓和程蝶衣分別舞臺22年后,這把劍讓程蝶衣完成了他從一而終的理想追求。
一把劍,串起了三人情感起伏跌宕的每個過程。
(二)傘
傘
傘出現在討論戲劇改革的一幕中,程蝶衣堅持著自己對京劇藝術的認識,段小樓有心附和,剛要講話,菊仙發出一聲高喊,并從看臺上擲給了他一柄紅傘,還說外面要下雨了。菊仙的這番努力沒有白費,段小樓回到戲臺上便說出了一番違心的言詞。菊仙又一次拯救了段小樓,但同時也將他推向背叛之路,在這里,“傘”無疑具有“保護傘”的含義,是一個關于躲避政治風雨的符號。
五、
《霸王別姬》是部博大精深的影片、全片無論是在情節編碼、導演手法,攝影手法、音響(音樂)細節處理等均居上乘、來說,一部偉大的電影(或其他藝術作品)必然有超越時代的本質意義,同時在藝術處理上也是高水平的。就這些方面來說,《霸王別姬》是無可比擬的。陳凱歌作為第五代導演領袖人物的地位也是不可否認,不可動搖的。